本文摘要:一、文史传统作为方法? 虽然奔着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这一主题,我原来提交的文章实在有点勉强。勉强不是因为敷衍,而是不喜欢抽象地谈方法,我喜欢奔着具体问题去,把有关方法的考量都置于其中。抽象谈方法很容易是虚晃一枪,最多令受众不明觉厉而
一、文史传统作为方法?
虽然奔着“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这一主题,我原来提交的文章实在有点勉强。勉强不是因为敷衍,而是不喜欢抽象地谈方法,我喜欢奔着具体问题去,把有关方法的考量都置于其中。抽象谈方法很容易是虚晃一枪,最多令受众“不明觉厉”而已。具体实在的研究,无论结论对错,受众都会用自己的经验来比较、分析和评判。我也不是反对方法,只是一直认为,人类总体上更关注后果,所谓“实质正义”,而真的不那么在意研究者的意图、程序或方法。而且,一个真正好的研究很少是因为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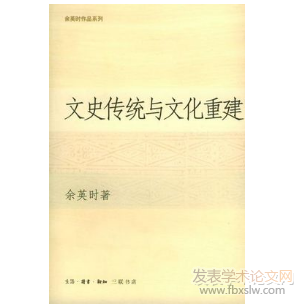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独门暗器,你抓住了,就可以稳步推进,保证成功。某些技术性演变、创新和发明确有可能遵循某种方法或程序来推进,但人文社科研究的,甚至自然科学的,重要发现和创新不仅不可能因遵循了什么方法,相反,更可能是某项发现会引发方法创新;多出一种方法,甚至置换了之前行之有效的方法。有许多研究发现甚至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好听的说法叫做“神龙见头不见尾”。张五常说,如果科斯不是一脚踩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例子(无线电频率相互干扰),可能今天都没谁注意到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①这种情况其实不少。
研究的精妙只可能在具体研究的精细分析论述表达中充分体现,有时作者未必自觉,甚至并未有心让读者察觉。方法也都有个分寸或“边界”问题,这也不是方法本身可能回答的。如今统计学很讲求方法,很程序化,一步步都很清晰,但关键仍然是研究者提出了什么问题或猜想,碰到了什么材料和数据,否则就会“垃圾进,垃圾出”。
萨缪尔森引用萧伯纳的话:“能做科研的就做了,做不了的就爱倒腾科学方法。”②这话说得很对。方法最迷(惑)人的地方在于它似乎承诺了某种“普世性”。但只要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方法往往与时空相关,即是社会条件催生的。在有统计方法并积累了可利用的数据之前,文史哲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记录历史,其中甚至包括了编故事和传说。也因此会有柏拉图的理念,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办法;但也有诸如谶纬这种最终令人绝望的努力。还有早期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如社会调查、访谈等。
在我看来,这些方法基本都是当时条件下的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或者说因陋就简,也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努力,但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先想个方法,然后按部就班展开。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成本太高了。不出现文字,没历史记载,就不会有文本解读或阐释问题;正史中就不会大量借助很戏剧性的想象,例如“大禹治水”“烽火戏诸侯”“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导致今天的学人要甄别区分古文献中的历史记录和文学想象。
研究跨文化的或陌生的村落或社会,一定需要更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才能了解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熟悉其语言。若研究故乡,访谈和调查的必要性就大大弱化,乃至可以,也会更多甚至大量借助回忆或反思,尽管研究者一定要有另一种生活经验为参照。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尤其是《乡土中国》就非常典型,从他的写作发表过程来看,那就是反思的结果。③
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城市社会,才需要且可能用问卷调查,做统计分析。但随着海量数据的累积,我判断,曾经流行的问卷调查,很可能日薄西山了。人们今天很容易借助其他远比问卷更准确的渠道,不仅是大数据,甚至是全数据,来分析、判断、理解和应对一些问题,想想,可用来预判美国大选结果的“义乌指数”,比官方国内生产总值(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现状的“克强指数”(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的结合),以及新冠疫情中的“健康码”。
一些历史研究,当涉及考古时,则必须甚至主要借助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手段。重视方法,有时也是为了避免自身偏见,弱化受众的前见/偏见,减少无聊争议,但这并不总是行得通。有时,同样的方法,结论也没错,但只要结论与读者的前见、好恶,甚至就是意识形态抵牾,就不接受显然的结论。“史诗互证”,陈寅恪考订白居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失实,可谓博学,也精细,对其他相关研究可能也有意义。
但我就是觉得,这种矫情没意思。但许多人,连陈的一本书都没看过,就跟着赞扬;还说是首创,把诸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诗句都忘了。④郭沫若从“卷我屋上三重茅”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类的诗句中,指出杜甫的地主阶级意识。⑤我觉得这真很令人信服,尤其是那个“寒士”至少曾让少年时的我多了个维度理解当时只知整体化崇拜的“诗人”群体。而且杜甫有这种偏见,也没啥丢人的。但有不少人认定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是迎合之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有意义,但也不能太当真了。方法未必真是个或只是个“利器”。
二、必须面对现实和未来
中国文史传统一直是发展、延续和变化的。这个传统,明显是个人或群体的各种活动留下的文化痕迹,包括了文字以及其他各种方式的表达,但我的判断是,催生、塑造和维系这个传统的最大变量其实不是或至少主要不是这个传统本身,也不只与个人才华相关,更主要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以及发展出来的相应的科技能力。任何地方人们的生产生活组织方式都会很受地理影响。
中国这片土地不仅山川地形特殊,而且今天放眼来看,在地球上的位置特殊,气候也很特殊。历史中国的家、国、天下,不能仅视为一种思想例如儒家思想的产物,它们更可能就是在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中,这片土地上的人一直面临的麻烦和问题。中原的地理地形,催生了各地的农耕,形成主要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农耕村落,“家”。但内忧,即黄淮海河流域的广义治水,以及外患,即农耕区与周边广大区域内非农耕族群的冲突,促成以村落为基础必须且逐步整合成政治经济文化日渐统一的农耕的“国”,进而反衬出其周边非农耕的“天下”。
历史中国,分分合合,时分时合,逐渐融合。围绕着这些一直令人纠结的麻烦,中国政治文化精英,并不只是儒家如孟子,形成了围绕家、国、天下展开的一系列话语和话语实践。后世历代政治文化精英也不得不以话语回应、以制度应对这三大问题。历史中国的文史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片土地,尤其是中原农耕文明的思想文化产物,有助于创造和稳定家、国、天下的基本制度和格局。
一方面“天不变”,只要经济生产方式不变,“道亦不变”,制度发生的机制及应对原则很难改变。但另一方面是,随着各种变量的累积、交流和发生,又总会促使社会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和变化,包括了淘汰和更替。文史传统也是如此。今天我们说的文史哲传统就是现代中国人对历史中国文史(或经史子集)传统的一个重构,因为虽然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哲学性质的思考和表达,典型如老子的箴言,但很难说有作为学科的“哲”。这个传统今天肯定会继续发展和变化。
不是因为时间本身很神奇,也不仅因为现当代的国际学术交流,最大的变量其实是20世纪以来中国自身的变化,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科学技术化,大大改变了人和社会的知识甚或文明需求。这种改变是制度结构性的,不是单线进化的,即便有人希望是进化演进的。换言之,这个变化未必是任何确定意义上的优胜劣汰,而更多是结构需求的转换。我们即便努力,也很难甚至无法早早预知和有效应对。例如,如今纸质书的阅读明显减少,甚至会继续衰微,但其他方式,包括我不习惯的抖音,交流、交换或传播的信息,以及人们对信息的自主汲取、追求和创造,一直会增加。
具体说来,首先是文,不只是古代的诗文曲赋,甚至近现代新文学,都在改变,有些甚至就是直接衰落了,乃至哪天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无论怎样干预,也只有点安慰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就逐渐失去轰动效应,那还主要是“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小说、新诗和戏剧;20世纪90年代大为流行的金庸作品,如今也开始远去。中国法学界也算有过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所谓文学中的法律,多年后才发现,从一开始,那就是个赝品,其实主要是电影中的法律,而不是传统的文学——小说和戏剧。
但这未必可悲。换一个角度看,这意味着,今天的文艺已不再承担那么多社会教化功能了,这也许部分就是法治的结果。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可能会为此困惑,不得不转行研究文化、传媒、电视剧/网剧、社会思潮等。前面已提到,传统中国的“哲”很可疑。在我这个外行看来,这个“哲”更像现代学人对中国文明,尤其是早期的重要思想家的智慧的阐释或重述,无论是否以西方学术传统做参照。将之定义为“哲学”,填补了一个空白,没人反对,也没法反对。但说那是古人的思想或智慧,没错,称其为“经学”也没大错。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哲学/思想/智慧/箴言与今天有多少关系呢?
如何勾连,如何附会,如何延续或推进?相比之下,在文史哲三科中,史学是发展最好的。实际上,自近代以来,历史研究就已大大拓展并且改观了,改变了传统中国主要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展开的历史。历史地理、经济史、民族史、边疆史以及考古等都使历史研究日益实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素也因此得以逐步但全面渗透历史研究。历史研究也向其他学科蔓延,直至催生了诸如考古这样独立的学科。
这一分析令我很怀疑有一个作为或可以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这就是前面我一直用“文史传统”的缘故,并且,在近代之前,这也一直是农耕时代的产物。随着20世纪以来中国巨大和伟大的变革,这个传统与当代中国的文化距离拉大了,许多人都觉得陌生。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文史传统曾有助于应对(主要还不是研究)历史中国的某些问题,也仍可能有助于今天部分文史或社科学者研究历史中国的某些问题,但如何用这个传统来研究当今那些被人们认为属于文史哲领域的问题?它似乎不大可能普遍、有效且成功地用于研究我们面对的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三、必须超越方法
文史传统有消长,这却不意味——即便可以——应当摒弃中国的文史传统。当今,研究中国需要创造,也必定会有创造。这个创造也正在发生,即这个文史(哲)传统的蜕变、发展和丰富。因为这个时代需要,并为这种创造提供了可能。文史哲传统一定会在我们前行中继续,但不能,也不应,只是作为方法。我不排斥“为己之学”,这类表达中不仅有某些重要的洞察和见识,也还可能分别地或共同地承载了某些我们目前还无法察知的重要信息。即便真的没有苏东坡所说的那种“李太白之乐”,留着也无害,无妨。
然而,基于知识的社会功用,也基于今天很多学人承担着传授或普及知识的责任,因此有必要也有可能基于更经验的传统来甄别和重述,进而可能通过各种研究来重构和拓展中国文史传统的某些命题,并予以系统理论表述。其中肯定包括方法,但绝不限于,甚至主要部分不会只是方法。例如,道家的老子和法家都为今天人文社科研究者提供了一些方法指南。我就非常喜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说法。⑦
除了可以理解为“一视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外,这也是个重要的方法提示,即研究过程中要避免把个人偏好或社会理想直接搬进来,或将之“翻译”为事实,尤其是别总想着“为天地立心”。政治文化精英个人有理想追求和道德勇气重要也必要,但会做事、能做成事更重要。
做事的麻烦在我看来主要还不是有没有理想和勇气,而是有什么资源,以及能不能具体务实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甚或,一定要理解,有许多问题,早先那可能是真没法子解决,当时的政治文化精英也就只能唱点高调,行行“礼数”。想想古代,每年仲春亥日,皇帝率百官祭祀先农神,亲耕一亩三分地。这种礼仪发生的最重要原因,在我看来,并非古人真的相信有“先农”神,或因为西周传统的神圣,而更可能是传统农耕中国的中央政府没有其他现实可行且能有效激励农耕的政治、文化、技术手段和措施,只能摆个祭祀先农的仪式,其实际功能大致等于今天中央向全国各地发个“一号文件”。
如果这个解说还有点道理,那么,促成这一祭祀发生的其实是社会功利,而不是皇帝和百官的信仰。如果我们今天只是从史书记录或前人解说的层面关注这个传统,追溯这个“礼”的源起,甚或主张照葫芦画瓢,那就是邯郸学步、刻舟求剑。今天,中央政府会发文件,但其关注的不仅有春耕,还有夏种,也更在意中央和各地对农机、化肥、农药和种子的调配,关注水利建设等。
四、也必须超越中国
真的,这可以超越中国。我的意思是,或可以用家、国、天下来理解欧洲或其他文明。现代欧洲各国人,日常生活在各自社区或各自业内(这就是他们的“家”),作为公民他们生活在各民族国家(他们的“国”),但这些国家大致分享了基督教文明(他们的“天下”)。或还可用此框架来勾勒和理解伊斯兰世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正教社会(俄罗斯、白俄罗斯、东乌克兰以及塞尔维亚等)、南亚次大陆、美国和“五眼联盟”以及拉美各国等。其实,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大致就是以这种方式理解世界的。
文史论文范例:从《文史通义书教》看章学诚的史意
有别于亨廷顿,我只是不认为美英能与今天欧陆各国(俄罗斯等国除外)利益持续一致,持久维系一个统一的西方文明。因为如果西方文明能包括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中西欧,那么似乎就没有理由不包括当代日本——亨廷顿认为日本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明,但无论历史还是今天,在我看来都很难成立,甚至这个框架或还可能解说美国今天面临的一些问题。
我不是说家、国、天下的框架正确,更好,更值得推荐。概念只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工具,不可能取代我们更精细的考察研究。我说的只是,从特定时空也即历史中国扒拉出来的家、国、天下这类概念,不仅能从某个维度解说历史中国,预测今天和未来中国,或有可能超越催生这个概念的那个特定时空,即农耕中国。这是我对中国文史传统的更高但不是没有可能达到的一个学术期待。
作者:苏力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5921.html
